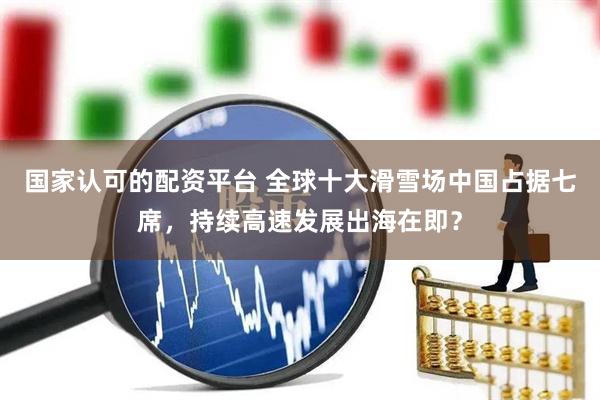火车到站的那个瞬间国家认可的配资平台,我以为自己闻到了钱的味道。
那是一股混杂着潮湿海风、滚烫尘土和无数人汗水的味道。
1991年的深圳,像一个巨大的、烧得通红的工地。
我叫陈进,十九岁,兜里揣着爹妈凑的四百块钱,还有我那个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爹,在我出门前,塞给我的一句硬邦邦的话。
他说,混不出个人样,就别回来了。
我当时梗着脖子,觉得这话多余。
我,陈进,高中毕业,在我们那个小县城也算个文化人,来深圳,还能被尿憋死?
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巴掌。
不,是左右开弓,把我扇得找不着北。
介绍所门口的人比菜市场的苍蝇还多,每一个都用审视的、怀疑的、麻木的眼神打量你。
工厂招工,手慢一点,名额就没了。
工地上搬砖,我这身板,干不过那些膀大腰圆的北方汉子。
不到半个月,四百块钱就见了底。
住最便宜的通铺,每天两个馒头,连咸菜都成了奢侈品。
更要命的是,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晚上,我揣在内兜里剩下的三十多块钱,被偷了。
那是我最后的尊严。
我坐在一个叫深南大道的路边,看着车来车往,那些车灯像流星一样划过,每一颗都好像在嘲笑我。
我成了个真正的流浪汉。
白天在人才市场附近游荡,希望能捡个漏,晚上就找个天桥底下缩着。
我睡的那个天桥,能看到不远处一栋高楼上巨大的电子钟。
红色的数字,一秒一秒地跳。
那不是时间,那是我正在燃烧的、一文不值的青春。
蚊子像轰炸机一样在耳边嗡嗡作响,肚子饿得咕咕叫,比蚊子声还响。
我开始后悔。
后悔为什么要来这个鬼地方。
后悔为什么不听我妈的话,在县城找个安稳事做。
可我知道,我回不去了。
不是没路费,是没脸。
就在我饿得眼冒金星,觉得可能就要这么死在深圳的某个角落时,他出现了。
他推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堆满了纸箱和塑料瓶。
车链子“嘎吱嘎吱”地响,像个得了哮喘病的老头。
他停在我面前,昏暗的路灯把他本就黝黑的脸照得更加模糊。
一股子汗味和废品的馊味混在一起,扑面而来。
“后生仔,哪儿的人啊?”
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口音,听不出是哪儿的。
我没力气回答,只是警惕地看着他。
“没吃饭吧?”
他又问,然后从挂在车把上的一个布袋里,掏出一个还带着温热的馒头。
白花花的,在我眼里,比金元宝还晃眼。
我咽了口唾沫,唾沫都像是刀子,刮得喉咙生疼。
他把馒头递给我。
“吃吧。”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
狼吞虎咽。
噎得直翻白眼,他拧开一个军用水壶递给我,我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
水是温的。
“看你在这好几天了。”他说,自己也靠在桥墩上,点了根烟,是那种最便宜的红棉牌香烟,烟雾呛人。
“找不着活?”
我点了点头,嘴里塞满了馒头,说不出话。
“想不想干活?”
我眼睛一亮,猛地抬头看他。
他指了指自己那辆破三轮。
“跟我干。”
我愣住了。
收破烂?
我陈进,好歹读过高中,跑到深圳来收破烂?
这要是传回老家,我爹的脸往哪搁?
他看出了我的犹豫,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
“怎么,看不起?”
他吸了口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暗。
“我跟你说,后生仔,在这深圳,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能让你吃饱饭的,才是真家伙。”
他顿了顿,看着我说。
“跟我干,我教你。”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手里剩下的半个馒头。
那半个馒头,就是我的命。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干。”
他就这样成了我师父,虽然他从不让我这么叫。
他让我叫他彪叔。
彪叔,一个收废品的。
这就是我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
第二天,天还没亮,彪叔就用脚把我踹醒了。
“起来!太阳晒屁股了还睡!”
我揉着眼睛爬起来,天边才泛起一点鱼肚白。
深圳的清晨,带着一股凉意。
彪叔已经收拾好了他的三轮车,扔给我一副脏兮兮的帆布手套。
“戴上,别把手划了。”
那手套又硬又臭,上面沾满了不知名的污渍。
我嫌弃地戴上,跟着他嘎吱作响的三轮车,走进了这个城市的背面。
我们穿过宽阔的大马路,拐进那些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巷子。
城中村。
握手楼挤得密不透风,天空被切割成一条条狭长的布。
空气里弥漫着下水道、剩饭剩菜和廉价洗发水的混合气味。
彪叔告诉我,我们的“地盘”是这附近几个小区和写字楼的垃圾站。
“收废品,不是光有力气就行的,得用脑子。”
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上课。
“你得知道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不值钱。”
“纸皮子分好坏,黄板纸最值钱,报纸次之,那些带塑料膜的,价钱就得往下压。”
“塑料瓶,看底下的标,1号、2号、5号,价钱都不一样。”
“还有铜,铝,铁,那才是大头。”
他像个将军在巡视自己的领地,熟练地跟各个垃圾站的清洁工打招呼,递上一根烟,说几句不咸不淡的笑话。
那些清洁工就会把分好类的纸皮和瓶子优先卖给他。
“这叫人脉。”彪叔吐了个烟圈,对我挑了挑眉毛。
我的第一天工作,就是跟在一堆发馊的垃圾里,把纸板、塑料瓶、易拉罐分开。
那味道,熏得我差点把昨天的馒头都吐出来。
手套很快就磨破了,手上被纸板划出好几道口子,火辣辣地疼。
一天下来,我累得像条死狗,腰都直不起来。
晚上,我们把满满一三轮车的废品拉到一个更大的废品收购站。
过磅,算钱。
彪to叔捏着一沓零零碎碎的票子,数了数,递给我五块钱。
“今天的工钱。”
五块钱。
我捏着那张又软又旧的票子,心里五味杂陈。
在老家,我爹在田里干一天,也挣不到五块钱。
可是在深圳,五块钱,能干什么?
买十个馒头。
这就是我一天的价值。
彪叔带我回他住的地方。
那是在城中村最深处,一个用铁皮和石棉瓦搭起来的棚子。
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破桌子,还有一个黑乎乎的煤油炉。
“晚上你睡床,我打地铺。”他说。
我看着那张油腻腻的木板床,实在没勇气躺上去。
彪叔从一个蛇皮袋里抓了两把米,扔进锅里,倒了水,开始煮粥。
又从一个咸菜坛子里捞出几根咸菜。
“吃饭。”
我们就着昏暗的灯泡,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喝着白粥,嚼着咸得发苦的咸菜。
我从来没觉得白粥这么好喝过。
“小子,觉得委屈?”彪叔突然问。
我没说话。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比你还惨。”他自顾自地说起来,“睡过工地水泥管,三天没吃过一顿饭,为了个馒头跟野狗抢食。”
我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这地方,吃人。”
“你想留下来,就得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狠。”
“对自己狠。”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一夜没睡。
棚子外面,是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
夫妻的吵架声,小孩的哭闹声,隔壁麻将馆哗啦啦的洗牌声。
这些声音,就是深圳的脉搏。
真实,粗粝,充满了生命力。
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没那么惨了。
至少,我有一张床,有一碗热粥,还有五块钱的工钱。
我,陈进,还活着。
跟着彪叔干了半个月,我基本上掌握了收废品的门道。
我知道了哪个小区的垃圾站油水最足,哪个写字楼的废纸质量最高。
我也学会了怎么跟人讨价还价,怎么用笑脸和香烟去搞好关系。
我的手掌结了茧,皮肤晒得黝黑,身上的衣服永远都带着一股馊味。
我已经很久没照过镜子了。
我怕看到镜子里那个又黑又瘦,眼神麻木的自己。
那不是我陈进。
可每天晚上,数着口袋里又多出来的几块钱,我又觉得,这就是我陈进。
一个在深圳为了活下去,什么都肯干的陈进。
彪叔对我要求很严。
“脑子要活!”他总是敲着我的脑袋,“收废品,收的是信息!”
“你看这家工厂,最近扔出来的废铁屑特别多,说明什么?”
我摇头。
“说明他们订单多,在加班加点干!这种厂子,以后肯定有大东西出来!”
“你看那栋写字楼,扔出来的全是碎纸机里出来的纸条,说明什么?”
我还是摇头。
“说明是保密单位,或者律师楼、会计所。这种地方,电脑、打印机更新换代快,都是好东西!”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第一次发现,收破烂,原来还有这么多学问。
彪叔不光教我这些,还教我认字。
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堆旧报纸,逼着我每天晚上念。
“你个高中生,字都认不全,丢不丢人?”
他自己其实也认不了几个字,就指着标题让我念。
我念错了,他就拿根小树枝抽我的手心。
“脑子!脑子是好东西!别让它生锈了!”
我很不理解。
一个收破爛的,认那么多字干嘛?
直到有一天,我们收了一堆旧书。
里面有一本《企业管理入门》。
我当笑话一样念给彪叔听。
“什么叫成本控制,什么叫现金流……”
彪叔听得特别认真,还不停地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才隐约觉得,彪叔,可能不只是想当个收破爛的。
我们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彪叔不知道从哪儿凑钱,把他的破三轮换成了一辆二手的机动三轮车。
“鸟枪换炮了!”他拍着崭新的车斗,笑得合不拢嘴。
有了车,我们能跑更远的地方,拉更多的货。
我们不再只局限于那个小小的城中村。
整个深圳,在地图上,都成了我们的猎场。
那天,我们在一个高档小区收废品。
我看到了阿玲。
她提着一袋垃圾,从一栋漂亮的单元楼里走出来。
穿着一身干净的工厂制服,头发扎成马尾,皮肤白净。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
我也愣住了。
我们是老乡,在来深圳的火车上认识的。
当时我们聊了很多,聊家乡,聊梦想。
她说她要去电子厂当女工,攒钱回家盖房子。
我说我要在深圳发大财,开公司,当老板。
现在,她穿着体面的工服,我穿着一身馊臭的破烂。
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垃圾桶,也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她的眼神里,有惊讶,有同情,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下意识地想躲。
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这副鬼样子。
“陈进?”她还是认出了我。
我低下头,嗯了一声,脸烧得通红。
“你……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指了指身后的三轮车。
“收……收废品。”
这三个字,像三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能感觉到彪叔在旁边看着我们。
阿玲的表情很复杂。
“挺好的,靠自己力气吃饭,不丢人。”她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我知道,这是安慰。
“你呢?在哪个厂?”我没话找话。
“就在附近的赛格电子厂,做流水线。”
“哦。”
然后,又是沉默。
她把手里的垃圾袋扔进垃圾桶。
“我……我上班要迟到了,先走了。”
“好。”
她转身走了,马尾辫在身后一甩一甩。
我一直看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在拐角。
“小子,看上啦?”彪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没说话,心里堵得慌。
“看上了就去追啊!”彪叔拍了我一巴掌,“收破烂怎么了?收破烂就不能娶媳妇了?”
“她不一样。”我说。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彪叔不屑地说,“你现在是收破烂的,不代表你一辈子都是收破烂的。”
“记住,男人,得有志气。”
“钱,就是男人的志气。”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
脑子里全是阿玲的样子,和她那复杂的眼神。
还有彪叔那句话。
钱,就是男人的志气。
我捏紧了拳头。
我陈进,不能一辈子当个收破烂的。
我得挣钱。
挣大钱。
我要让阿玲,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看看。
我陈进,不是废物。
从那天起,我像变了个人。
我不再抱怨工作的脏和累。
我每天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
我把彪叔教我的那些“道道”全都记在心里,并且举一反三。
我开始主动去跟那些工厂的采购、仓库的管理员拉关系。
我不抽烟,就把彪叔给我的烟钱省下来,买点水果,买点汽水,送给他们。
一开始,人家都看不起我这个收破烂的。
但伸手不打笑脸人,来往多了,也就熟了。
他们有什么要处理的废料,会第一个想到我。
有一次,一个五金厂的仓库主管老王,急着要处理一批泡了水的螺丝。
别的废品站都嫌麻烦,不愿意收。
我知道这批螺丝虽然生了锈,但都是上好的钢材,回炉重造,价值不菲。
我跟彪叔商量,用我们当时几乎所有的积蓄,把这批货吃了下来。
我们俩,没日没夜地把那些螺丝一颗一颗地从水里捞出来,晾干,装袋。
整整干了三天三夜。
最后,这批货卖出去,我们净赚了三千块。
三千块!
那是我当时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拿着那沓厚厚的钱,我的手都在抖。
彪叔把钱分成两半,一半推给我。
“你的。”
“不,彪叔,这太多了,主意是你想的,力气是咱俩一起出的……”
“拿着!”彪彪叔眼睛一瞪,“我说你应得的,你就应得!以后,我们赚的钱,都这么分。”
我看着他,眼眶有点热。
他不是我师父,也不是我老板。
他像我哥,像我爹。
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们不再是小打小闹地收点纸皮瓶子。
我们开始专门做工厂的废料回收。
我们租了一个小仓库,雇了两个人,专门负责分拣和打包。
我也不再跟着车出去跑了。
我每天穿着一身最干净的衣服,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梭在深圳的各个工业区。
我跟那些厂长、经理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谈生意。
他们一开始都觉得奇怪,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怎么做起了这门生意。
但我懂行,价格公道,做事靠谱,慢慢地,他们也都认可了我。
我有了自己的名片。
“宏达再生资源回收部 经理 陈进”
每次递出名片,我都觉得底气足了一点。
我开始存钱。
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存够一万块。
一万块,在1991年,是一笔巨款。
我想,等我存够了一万块,我就有底气去找阿玲了。
我会告诉她,我不再是那个睡天桥、收破烂的陈进了。
我是一个经理。
一个有事业的男人。
我时常会去赛格电子厂门口等她。
我不敢靠得太近,就远远地看着。
看她和一群女工有说有笑地走出来。
看她骑着一辆小巧的自行车,消失在人海里。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骑车追了上去。
“阿玲!”
她回头,看到是我,有些惊讶。
“陈进?你怎么在这?”
“我……我路过。”我撒了个谎。
“你现在……还在做那个?”她问得有些小心翼翼。
“嗯,还在做。”我点了点头,“不过现在做得大了点,自己开了个小……小档口。”
我不敢说公司,怕她觉得我吹牛。
“那挺好的,你真厉害。”她笑了,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那天,我送她回她们的员工宿舍。
我们聊了很多。
聊工作,聊深圳,聊未来。
我发现,她其实过得也并不开心。
流水线的工作枯燥乏味,每天十几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宿舍里人多嘴杂,勾心斗角。
她也想改变,但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真羡慕你,自己做老板。”她由衷地说。
那一刻,我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值了。
我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但生活,总是在你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给你来一记重拳。
那天,我们的仓库失火了。
火是从隔壁一个做喷漆的小作坊烧过来的。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整个仓库已经成了一片火海。
我们所有的货,我们所有的心血,都在那场大火里,化为了灰烬。
消防车呜啦呜啦地来了又走了。
只留下一片断壁残垣和刺鼻的焦糊味。
我瘫坐在地上,看着眼前的一切,脑子一片空白。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我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全都投在这批货里了。
我还欠着外面一屁股的债。
我们一夜之间,从一个冉冉升起的小老板,又变回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甚至,还不如从前。
因为我们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彪叔蹲在我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他的背,在那一刻,好像佝偻了很多。
那晚,我们俩谁也没说话。
第二天,我雇的两个工人来找我们。
他们是来要工钱的。
我拿不出钱。
他们开始骂骂咧咧,说我们是骗子,是黑心老板。
周围的邻居也都围过来看热闹,指指点点。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
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是彪叔站了出来。
他不知道从哪里变出几百块钱,塞到那两个工人手里。
“这是你们这个月的工钱,我们现在确实没钱了,剩下的,等我们缓过来,一定补给你们。”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力。
那两个人拿着钱,没再说什么,走了。
人群也散了。
“彪叔,你哪来的钱?”我问他。
那是他准备寄回家给他老娘的钱。
他全拿出来了。
“我们还没输。”彪叔看着我,眼睛里布满血丝,但却异常明亮。
“货没了,可以再收。”
“钱没了,可以再挣。”
“只要人还在,就有希望。”
我看着他,这个只比我大十几岁的男人,这个带我入行的收废品的大叔。
我突然觉得,天,塌不下来。
我们从头再来。
我们卖掉了那辆机动三轮车,还清了一部分债务。
然后,我们又推上了那辆最开始的破旧三轮车。
回到了起点。
不一样的是,我的心里,不再有迷茫和自卑。
我清楚地知道我要做什么,该怎么做。
我们比以前更拼命。
白天收废品,晚上就去夜市摆地摊,卖些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小玩意儿。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人很快就瘦脱了形。
但我心里,憋着一股劲。
我一定要把失去的,都拿回来。
阿玲知道了我的事。
她来找我。
在我摆地摊的夜市。
她看到我,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我。
“这里面是我存的钱,虽然不多,你先拿着应急。”
我捏着那个信封,很厚。
我知道,这可能是她所有的积蓄。
我把信封推了回去。
“我不能要。”
“为什么?”她急了,“我们是老乡,是朋友,互相帮忙不是应该的吗?”
“正因为是朋友,我才不能要。”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阿玲,你相信我,我很快就能站起来。”
“这点困难,打不倒我陈进。”
她定定地看了我很久,最后,把信封收了回去。
“好,我相信你。”
她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但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转机,来得很突然。
那天,彪叔的一个老乡,从老家过来投奔他。
那个老乡以前在一家国营的电子元件厂当过技术员。
厂子倒闭了,他也下了岗。
我们请他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说起他们厂里,有一大批积压的电子元件。
都是些电容、电阻、二极管之类的东西。
因为是好几年前的库存,型号老旧,一直处理不掉,就堆在仓库里当废品。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问他,那些元件,具体是什么型号。
他报了几个。
我不是很懂,但我隐约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
那时候,深圳的华强北,已经开始有了电子市场的雏形。
无数搞电子产品的人,都在那里淘金。
他们需要大量的电子元件。
我拉着彪叔,连夜坐火车,去了他老乡的那个厂子。
那是一个已经停产的破败工厂。
仓库里,堆满了积灰的纸箱。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崭新的电子元件,包装都还没拆。
厂长是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正为这批库存发愁。
当废品卖,不值几个钱。
当正品卖,又没人要。
我跟他谈。
我说,我愿意出五万块,把这批货全包了。
五万块。
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跟彪生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还不到五千。
厂长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小兄弟,你不是开玩笑吧?你有五万块?”
“我现在没有,但你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给你凑齐。”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
我给厂长画了个大饼。
我说深圳的电子市场有多火爆,这些元件虽然型号老,但很多维修和仿制的业务都需要。
我说得口干舌燥,自己都快信了。
最后,厂长被我说动了。
可能是因为,除了我,再也没有第二个傻子愿意接这个盘。
他同意了。
但他有个条件,我必须先交五千块的定金。
如果一个月内凑不齐尾款,定金不退。
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凑了五千块,签了合同。
回到深圳,我跟彪叔都觉得,自己疯了。
一个月,四万五千块。
上哪儿去弄?
彪叔把他老家的房子都押上了,准备去借高利贷。
我拦住了他。
我说,彪叔,这事,不能这么干。
我们得想别的办法。
我拿着从厂里带回来的样品,一头扎进了华强北。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见人就问,见店铺就钻。
“老板,要不要电子元件?老型号,便宜。”
大多数人,都把我当骗子,或者。
吃了无数的闭门羹,受了无数的白眼。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连一个元件都没卖出去。
我开始绝望了。
难道,我们真的要血本无归,还要背上一屁股债?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香港老板。
他姓李,在华强北开了个小档口,专门做电子产品维修。
他看了我的样品,眼睛亮了。
“靓仔,你这些货,还有多少?”
“很多,你要多少,我给你弄多少。”我看到了希望。
李老板告诉我,我手里的这批货,虽然型号老,但在香港和国外的一些市场上,还有需求。
很多老旧的设备,都需要用这些元件来维修。
而且,其中有几种,因为已经停产,成了稀缺货,价格很高。
我感觉自己像是中了头彩。
我跟李老板谈了个协议。
他帮我销货,我给他提成。
并且,他先预付了我两万块的定价。
拿着那两万块钱,我激动得差点哭了。
我立刻给彪叔打电话。
“彪叔!我们有救了!”
剩下的两万五千块,我们想尽了办法。
彪叔找他所有的老乡借。
我去找阿玲。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我说,阿玲,你愿不愿意赌一把?
如果你信我,把你的钱借给我。
等我赚了钱,我加倍还你。
如果你不信我,也没关系,我能理解。
阿玲看着我,看了很久。
她没说话,转身回了宿舍。
过了一会儿,她拿出一个布包,递给我。
里面是她所有的积蓄,还有她问遍了所有工友借来的钱。
一共八千块。
“陈进,我不是借给你。”
她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
“我是投给你。”
“我相信你。”
那一刻,我发誓,我陈进这辈子,绝不负她。
我们终于凑够了钱。
我们把那批货,从那个破败的国营工厂,拉回了深圳。
我们租了个更大的仓库。
李老板的销售渠道非常厉害。
我们的货,源源不断地销往香港、东南亚。
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第一个月,我们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第二个月,我们赚了十万。
第三个月,二十万。
半年后,我们成了华强北小有名气的“电子大王”。
我们不再是收破烂的了。
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深进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的“深”,陈进的“进”。
我当上了总经理。
彪叔当了董事长。
虽然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但他坐在那里,就是公司的定海神针。
我们从城中村的铁皮棚里搬了出来。
我在一个高档小区买了房。
当我拿着钥匙,站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时,我还有点不敢相信。
这一切,像做梦一样。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阿玲。
我开着一辆新买的桑塔纳,停在她宿舍楼下。
我捧着一大束玫瑰花。
周围的人都在看。
阿玲从楼上下来,看到我,脸红了。
“陈进,你这是干什么?”
我单膝跪地,拿出我准备了很久的戒指。
“阿玲,嫁给我。”
我说不出太多花言巧语。
我只知道,这个女人,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把她的一切都给了我。
她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
阿玲哭了。
她一边哭,一边点头。
周围响起了一片掌声和口哨声。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风光。
彪叔是我的证婚人。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
但他一开口,还是那股熟悉的,带着泥土味的口音。
他说:“我没啥文化,不会说好听的。”
“我就知道,陈进这小子,是个好样的。”
“阿玲,你嫁给他,没错。”
说着说着,他一个大老爷们,眼眶也红了。
我也哭了。
我想起了那个睡在天桥下的夜晚。
想起了那个递给我馒头的,收破烂的大叔。
想起了那句,“跟我干,我教你。”
他教我的,不仅仅是怎么收废品,怎么做生意。
他教我的是,怎么在这个吃人的城市里,活下去,并且,活出个人样。
婚后,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们从单纯的元器件贸易,开始涉足电子产品的生产。
我们建了自己的工厂。
阿玲辞掉了流水线的工作,帮我管工厂的财务。
她很有天赋,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们有了孩子,一个男孩。
我给他取名叫陈念。
纪念我们那段艰苦,却又闪闪发光的岁月。
彪叔一直没有成家。
他说他习惯了一个人。
他把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转给了我。
自己只留了一小部分,拿着分红,过起了半退休的生活。
他喜欢上了钓鱼。
经常一个人,开着车,跑到水库边,一坐就是一天。
我知道,他有心事。
有一次,他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起了他的过去。
原来,他曾经也是个小老板,在老家开过一个砖厂。
后来因为被人骗了,赔得倾家荡产,老婆也跟他离了婚,带着孩子走了。
他万念俱灰,才一个人跑到深圳来。
他收废品,不仅仅是为了糊口。
他是在收那些被别人丢掉的希望。
他想看看,这些被丢掉的东西,能不能在他手里,重新变得有价值。
“陈进,你小子,就是我收回来的,最值钱的一块‘废品’。”他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
我也笑了,眼泪却流了下来。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深圳,已经从一个大工地,变成了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深南大道两旁,高楼林立,霓虹闪烁。
当年我睡过的那个天桥,早就被拆掉了。
我的公司,也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集团。
儿子陈念,大学毕业后,没有接我的班。
他有自己的想法,跑去做互联网,搞什么风险投资。
我看不懂,但我支持他。
就像当年,彪叔支持我一样。
我和阿玲,也开始慢慢老了。
她眼角有了皱纹,但笑起来,还是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很庆幸,当年在火车上,我主动跟她搭了话。
也很庆幸,在我最狼狈的时候,还能再遇到她。
有时候,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开车,在深圳的街头转悠。
我会路过华强北。
那里依然是人声鼎沸,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写满了欲望和焦虑。
我会路过那个我们曾经住过的城中村。
那里已经被推平,盖起了更漂亮的小区。
但空气里,仿佛还残留着当年那股复杂的味道。
我也会开到那个天桥曾经所在的位置。
停下车,摇下车窗,点一根烟。
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车河。
我常常会想,如果,1991年的那个晚上,没有遇到彪叔。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会饿死在那个天桥下。
可能会在某个工地上,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建筑工人。
可能会在某个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耗尽青春。
也可能会因为走投无路,走上邪路。
有无数种可能。
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人生,有时候,真的就是一步之差。
一个选择,一个遇见,就能改变所有的轨迹。
彪叔前几年走了。
走得很安详。
他把他的遗产,全都捐给了一个专门资助贫困学生的基金会。
他的遗嘱里说,知识,才是最值钱的“再生资源”。
我把他安葬在了深圳。
他说,他喜欢这里。
这里是他跌倒的地方,也是他重新站起来的地方。
墓碑上,我没有刻“董事长”之类的头衔。
我只刻了一行字。
“一个教人拾起希望的人。”
前几天,我开车路过一个立交桥。
看到一个年轻人,跟我当年一样,茫然地坐在桥洞里。
他的眼神,空洞,又带着一丝不甘。
我把车停在路边。
走过去,从后备箱拿了一箱水和一些面包。
我把东西放在他面前。
他警惕地看着我。
像极了当年的我。
我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
“后生仔,遇到难处了?”
“如果想找份活干,可以来找我。”
“从最底层干起,包吃包住。”
他愣愣地看着我,又看了看手里的名片。
我没再多说什么,转身走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但我希望,他能抓住这个机会。
就像当年,我抓住了彪叔递过来的那个馒头一样。
车子重新汇入车流。
收音机里,正放着一首老歌。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物。
我知道,我的路,还在脚下。
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个像我一样的陈进,怀揣着梦想而来。
也每天都有无数人,梦碎了,黯然离开。
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
这里是造梦工厂,也是欲望绞肉机。
但无论如何,我都感谢它。
感谢1991年的那个夏天。
感谢那个睡在天桥下的,饥肠辘辘的自己。
更感谢那个推着破三轮,对我说“跟我干,我教你”的,收废品的大叔。
他叫彪叔。
他是我一辈子的恩人。
鸿运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